Luye Global Staff E-magazine
2023年11月刊编者按:
吉迈生物是绿叶生命科学集团旗下的子公司,专注于开发针对癌症和严重传染病的基因药物。这个年轻的团队由一群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科学家组成,他们相识于疫情期间,通过线上会议和邮件沟通有条不紊地推进项目组工作。本月我们邀请到几位来自中美团队的员工代表,为我们讲述当科学理想遇上多元文化,会碰撞出怎样的思想火花。
Q: 感谢各位参加本月的员工采访,请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Tea: 我叫Teodelinda Mirabella。我于一年半前加入吉迈,担任高级总监,负责 mRNA 开发部门。从热那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在耶鲁大学医学院接受了博士后培训。之后又搬到了波士顿开始了在制药行业的职业生涯。我曾在多家公司工作过,包括 Wyss 研究所、Moderna、J&J 和其他小公司。除了家庭,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药品。

Lakshmi:我出生成长于印度,并在印度德里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在新西兰梅西大学和波士顿哈佛医学院接受博士后培训。我在药物开发行业有 20 多年的经验,擅长小分子和核酸疗法,包括先天性免疫受体激动剂和拮抗剂、 反义技术和 siRNA。我于 2020 年 11 月加入吉迈,担任寡核苷酸研发团队的副总监。

崔:我叫崔文燕,我的专业背景是天然药物化学硕士,毕业后一直从事核酸药物相关的鉴定、解析以及平台搭建工作。我于2020年6月加入了吉迈药物分析研发部,作为最早加入的员工之一,我参与了多个工作从零到一的交付,包括GalNac, Oligo以及mRNA从原料到制剂的搭建。很荣幸可以伴随公司一路成长,陪伴公司将项目推进到IND申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很多收获。

郎:我叫郎文杰,我是2022年化学生物学专业的应届博士毕业生,吉迈生物是我毕业后加入的第一个公司,目前就职于药物递送研发部。

Q:吉迈生物是一家相对年轻的公司,南京和波士顿团队之间的配合也开始于新冠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可以谈谈你们对彼此之间的初印象吗?
Lakshmi:最初我是忐忑的,不知道加入这样一个初创的跨国团队会面临什么。入职后,南京团队的同事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聪明、热心、友好、乐于接受意见和建议。
还记得初期我们经常利用周日晚上的时间和化学团队进行例会,当时我是团队中唯一的外籍且没有化学背景的女性成员。团队的伙伴们非常积极地分享在研究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他们尽力和我沟通,我们就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步分享思路和文献,共同寻找答案。有时我会在凌晨两三点收到南京同事们的邮件,我都会尽可能的尽早回复他们。我不希望因为时差而过多耽误他们的工作进程,可以说,我几乎全天候与化学、分析、工艺开发和配方团队保持交流。
今年六月,我有幸来到中国见到了南京的同事们,正如我对他们的初印象一样,我在南京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招待。我们参观了设备一流的南京实验室,了解了他们日常工作的情况。因为我是素食主义者,南京的同事们还特意为我准备了素食。工作之余我们还参加了团建,大家在一起开心地唱歌跳舞,吃烧烤,玩游戏,南京之行对我来说有一种家庭团聚的感觉。

中美团队在南京组织团建活动
Tea: 我在南京负责管理两个团队,一个是mRNA 合成团队,由南京团队的王德华领导,我们需要将 RNA 平台工作与工艺开发分开,一方面为了确保技术开发和专利保护,另一方面为后续的主要项目过渡到 GMP 生产提供基础。另一个是生物团队,这个部门的同事们比较年轻,团队组成更加的多元化。我们的团队中有很多优秀的人才,未来有潜力培养成为团队的领导者。我很高兴可以和这群热情勤奋的同事们一起工作。
今年六月,我们终于有机会来到南京和团队的伙伴们见面。虽然日常我们的沟通都是通过线上会议和邮件,但是我能感觉到彼此之间早已建立了情感连接,所以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就立刻给了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南京的同事们还组织了团建活动,我们在一起享受了美食,唱了卡拉OK,南京之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有着厚重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城市。
崔:虽然我加入公司只有三年多,但在吉迈也算是老员工了。刚开始中美两边的团队都处于初建阶段,我对于波士顿同事们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们对技术了解的深度以及对于国际视野认知的广度。最初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所有的沟通都只能通过线上,大家都在会上直接讨论技术相关问题,缺少了面对面对话的温度,我们之间仿佛只有工作的关系。但这种感觉在今年国际航班重新恢复后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在南京见到了波士顿团队的同事们:Teodelinda和Lakshmi。当我们面对面沟通时,你会发现原来他们都是那么逗趣的人,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冰冷的电脑屏幕与彼此互动,大家都面带微笑,时不时还会调侃几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中美团队成员在南京聚餐
郎:我所在的制剂部门日常主要和波士顿的初博士所带领的团队进行定期的组会沟通。今年6月,美国的同事们来到了南京,Lakshmi还给我们带了巧克力。她们在南京期间给我们做了一个关于HPV 2.0的技术分享,让我收获颇多,进一步了解到波士顿同事们日常所从事的工作。
Q: 中美团队在日常工作中是如何相互配合的呢?
郎:就像我刚才所说,日常我们需要和base在波士顿的初博士的团队配合。我们通常会从一些尝试性的实验开始,对于一些比较有意义的验证性实验,初博士的团队会先做广泛的探索,如果需要推进到技术转化,就会交由南京团队做一些技术跟进和验证。平时我们会组织每两周一次的组会,轮流进行技术上的交流和分享。
崔:谈到中美团队的分工,南京团队的工作更偏向于产品落地,所以我们的很多工作与合规性以及整体质量相关。我们现在所做的项目申报,很多时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波士顿团队的作用在于,他们能够以更广阔的视角,根据过往在美国申报的经验以及海外同行对于质量标准的控制给我们提出指导性意见。我们可以共同完成质量标准限度的设定,序列的最终敲定,以及确定最优选的质控方法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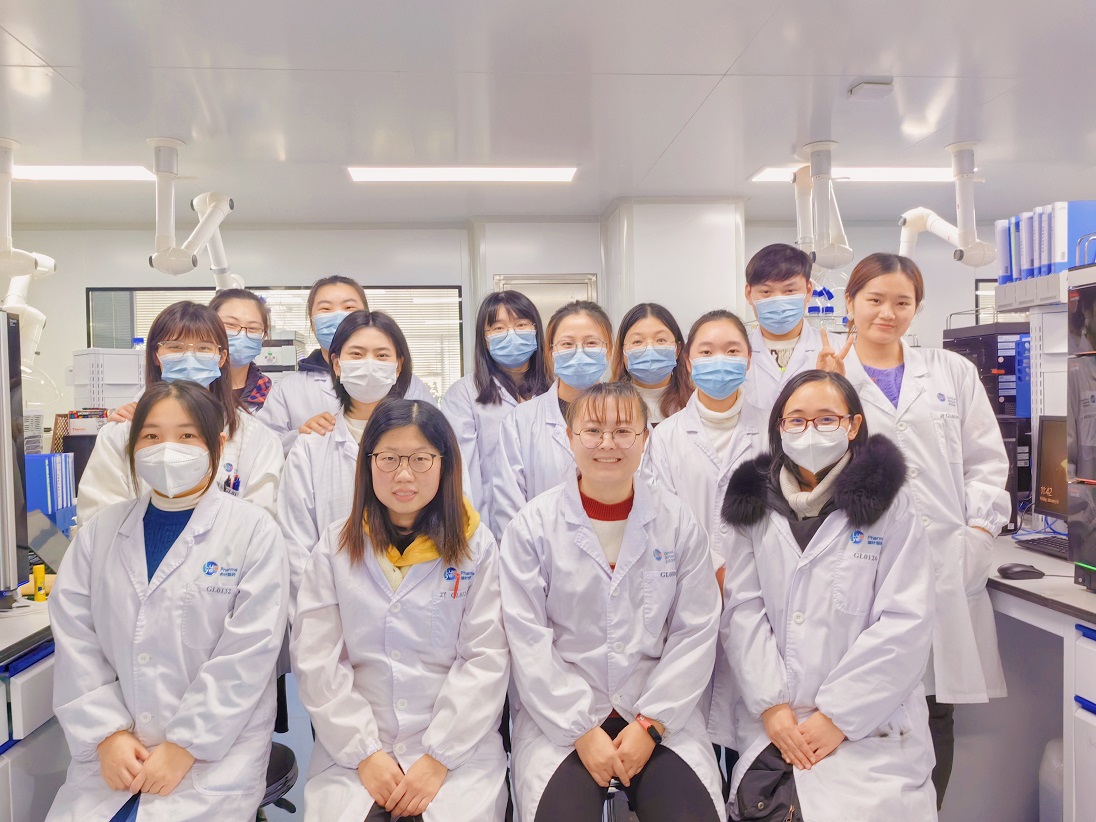
崔文燕及其团队合影
Tea: 中美两地有12小时的时差,所以客观上是存在一些挑战的。我们平时都会确保手机畅通,以便随时保持联系。中美团队一直保持着定期例会和按需开会的工作习惯,以便及时沟通项目进展和困难。我们一直保持着高效和开放的沟通,这样有助于灵活快速的决策。
Lakshmi:我们日常用邮件保持交流。如果他们有一些临时紧急的问题,也会用微信。中美团队定期召开月会,会上提供同声传译支持两边的交流。
Q: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两边的团队在配合初期会有哪些困难呢?你们是如何度过磨合期的?
Lakshmi: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但对我个人而言并不是问题,在我接受博士后培训期间,团队的同事们都来自不同国家,所以语言并不会给我造成太大困扰。我认为人与人的沟通有时可以通过情绪有所感知,尤其是在科学界,我们的很多讨论可以用图表予以辅助,此外翻译软件也起到了很大帮助。更幸运的是,现在吉迈的例会还配备了同声传译,我们的项目经理周肖楠也在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协调作用。另一个挑战是时差,但这只是在初期有些困扰,现在我早已习惯了晚上工作。
崔:客观来说,中美两个团队之间有12个小时的时差,大家经常需要晚上八九点开会,有时甚至连双休日也无法避免,在初期大家都会有些疲惫;其次两边团队的邮件沟通也因为时差的原因而有所影响,有时当我们急着需要等待答复时,对方可能还在休息时间;第三就是语言障碍,这需要我们花时间去不断锻炼。
但是三年的时间过去了,大家在时差这一问题上逐渐开始调和,收到邮件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晚间的会议也进行了调整,确保双方需要沟通的问题尽量在1-2小时内结束,现在的会议也都有了翻译支持,会后如果还有后续问题需要沟通,我们会通过邮件再次确认和落实。
郎:我曾经在新加坡有一年多的留学经历,当时的课题组研究也需要跨国合作,所以在跨国团队合作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经验的。关于时差,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例如我们日常和波士顿团队进行的例会,因为他们的团队只有2-3个人,我们这边参会的人员多一些,所以波士顿的同事们在时间上会做出一些牺牲,经常需要晚上参会。,
Tea: 除了时差之外,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 mRNA 对公司来说是一种新的模式。我们在团队合作的过程中都带着美好的心愿和互相信任的态度,这对于团队而言是最重要的。
Q:在跨国团队合作的过程中有什么收获?未来在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改善?
Lakshmi:在吉迈,跨部门合作已成为一种常态,我的工作就涉及多个部门的配合。我在这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就是持续不断地学习,每参加完一场会议,我都会从中学到新的知识和内容。我们的团队内一直保持着公开透明的交流氛围,无论实验结果好坏,我们都能坦诚沟通。
除此之外,我认为良好的沟通、团队互动创新、勤奋、信任、坚持不懈、牢固的关系和透明沟通可以克服一切障碍。我们的波士顿团队很小,但与南京的配合证明了一切皆有可能。最近团队在全力准备第一个项目的IND申报工作,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项目在探索阶段。我认为承认他人的辛勤努力非常重要。除非你对他人给予应有的肯定,否则你将永远无法达到顶峰。
我是在新冠期间加入了吉迈,那时质粒、细胞系、化学合成物和其他物品的运输受限于疫情管控而出现过一些延误,希望今后在这方面可以有所改善。另外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机会邀请南京的同事们来波士顿,我很乐意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办公。
Tea:我非常认可国际合作的模式,在这样一个充满包容性和多元化的环境中工作感觉很棒。吉迈将一群优秀的,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们聚集在一起,大家都各有所长,我认为现在南京和波士顿的团队已经实现了很好的整合。我们需要保持这种有机平衡,即波士顿团队负责研究型工作,南京团队负责开发类工作。
对于未来,我们需要尽可能消除语言障碍,我要勤练中文,南京的伙伴们也要多多练习英语口语。我希望我们能从现有的两个中心的模式转变为一个更加流畅整合的模式,使所有研发业务完全协调,但这也不完全取决于内部,外部环境也有影响,例如国际供应链,运输政策,人才吸引等。
郎:我们在吉迈的目标是将现有的项目从IND推向NDA,这就需要我们从小试推进到中试,再到生产,如果我们仅仅是着眼于闭门造车的形式,就无法拓宽自己的视野。和波士顿团队配合的收获在于,他们一直处于技术的前沿,可以接触到更多新鲜的讯息,并将这其中有新意的技术进行一轮初步探索后推荐给我们做下一轮验证,这样提升了整体的工作效率。对于未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项目推进到了IND阶段,接下来就需要新的项目来填充,所以我们要加速推进新项目的开发和探索。

郎文杰所在团队合影
崔:我觉得当两个团队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会带来思维的碰撞,拓宽我的思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对于未来,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美国团队技术桥头堡作用的优势。我们看到一些诺贝尔奖是在美国产生的,那里相对来说有更多的资源,这和我们“埋头拉车”式的看文献,做技术筛选是有很大不同的。所以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更好发挥美国团队的优势,提出更多可实施的,有新颖性和突破性的技术方案。
Q: 请分享你们对于未来的期望。
Tea:我们需要持续投入人才发展。对于很多尚未满足的医疗需求,我们需要时刻保持紧迫感,对于未来永远保持信心,背负使命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Lakshmi:对于生活我一直保持积极,我总是盼望着好消息,但也能坦然面对坏消息。吉迈现在面临很多挑战,我想如果能按照时间线推进工作,再加上更多资源,我们可以成功完成更多项目。如果一切顺利,我希望未来可以壮大团队。但如果一切不如所愿,我们也时刻准备好快速适应并应对公司的方向调整和新变化。吉迈团队的每个同事都身兼数职,大家都有能力灵活接受工作任务。希望我们能按时完成 IND 申请,并尽快启动临床试验。最重要的是,希望未来能为更多患者创造出安全、有效、负担得起的药物。
崔:加入吉迈团队的这三年,随着公司项目的发展,我确实收获了很多成长,希望可以把这些工作和经验继续推广,避免未来的工作走弯路。其次是进一步发挥中美两个团队各自的优势,让吉迈在未来可以有全方位的成长和突破。
郎:以前我在学校里学习的都是比较整体、实验类的知识,加入吉迈后,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学到了很多在以前没有机会学到的内容。未来我希望能有机会通过新项目进一步锻炼我的实践经验。希望我们的团队可以产生更多想法的激情碰撞。更希望吉迈未来越来越好,给我们提供更大的平台,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想去波士顿的团队看一看,了解他们的日常工作是怎样进行的。

